
一
离开父母,在别处生活,至今已经二十年了。
今年春节,我终于说服母亲,和我一起去旅游,这是二十年来的第一次。母亲是个从来不出门的人,父亲、姐姐、姐夫、外甥女轮番上阵做工作,母亲总算答应,“这是女儿的一片孝心哪,”母亲叹息说。
当时,我并没听懂这句话的潜台词,只为请动了母亲而欢呼雀跃。在外面漂了这么多年,终于可以带父母见识花花世界,享受现代文明,心里那块黑洞好似补上了一小块。
1月底,我在高铁站接到了父母。母亲的脸庞枯黄浮肿,身体佝偻,气色很差。我问母亲旅途是否顺利,她点点头,轻描淡写地说:“还好。”我放心了,没有再问下去。
旅程是我精心设计的。因为母亲行走不便,我问了很多朋友,都说带老人出去,坐邮轮是最好的选择,可免舟车劳顿,还吃喝玩乐一条龙。于是我订了海洋量子号的日韩航线,兴高采烈地带着父母登船。
第一天,风平浪静,母亲看不出有何异样。第二天夜里,风浪骤起,万吨巨轮不时剧烈摇晃。早上我来到父母的舱房,意外地发现母亲躺在床上,脸色发黑,头发蓬乱,双眼都凹陷了下去。父亲说,昨天夜里船开始颠簸,母亲吐了几次,恨不能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。吐完之后就是眩晕,到现在床都起不来了,更别说进食。“你妈体质差,平时连坐火车、地铁、公交都会晕,所以从来不出门。是我和她说,这么大的轮船,一定不会晃的。”父亲懊恼地说。
我这才知道,母亲的身体已经到了这个地步。才知道,她那句“这是女儿的孝心哪”是什么意思——我以为自己是在对母亲尽孝,但其实是母亲,强撑着虚弱的身体,来成全我的“孝心”,让我心里舒服一点。换句话说,我用我的“孝心”,把母亲绑架到了海上。
茫茫大海,无边无涯,船要漂上几天才能靠岸。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母亲硬扛。父亲耷拉着头坐在一边,嘟囔着他哪里也不去玩了。我坐在床头,握住母亲的手,心中百味杂陈。
舷窗外,几百只海鸥结队追逐着巨轮,无休无止;海面翻起洁白的巨浪,一下一下把轮船送上波峰。不知世事的女儿蹦跳着,拍手、欢呼。我却在想,要是我能变成海鸥多好,就能带着母亲逃离大海了。
二
曾经,在我心里,母亲是坚不可摧的存在。她从来就不是什么女汉子,她是个真正的汉子。
十三岁,跟着她的父亲拉板车。听说那是身强力壮的男人才能干的活计。母亲家当年也有一头小毛驴帮忙拉车,但不知怎地,那头驴没了,再后来,母亲就变成了那头驴。
十七岁,初中毕业,扛起铁锹和一群男人一起修铁路。工地上没有女人,只有苦力。赚得微薄的报酬,全部交给外婆养家。
三十几岁,在一家纺织商店当柜台长,经常需要出去进货。瘦小的母亲为了能随身带走堆积如山的货物,拿绳子一头捆住货,另一头勒在腕间拖着走。积年累月,她的腕管神经受到严重损害,后来,四十出头的时候,全身肌肉就开始萎缩,两只大拇指几乎完全报废,脚部的肌肉消失,行走时脚底的骨头直接在地上磨,像走在刀尖一般。
如果说,像男人一样劳作,强大的只是她的身体,那么她的内心,比大多数男性更加强悍。
二十五岁时,母亲和父亲结合了。父亲才华横溢,心高气傲,不甘心困在小镇一辈子。婚后不久,他就到千里之外打工。母亲只得独自一人挑起家庭的重担,恐怕她也没想到,这一挑就是十多年,直到八二年才与父亲团聚。
我们姐妹,基本上都是母亲独自生下并抚养长大的。她一边带着一串孩子,一边还要在纺织厂做女工,养活我们。十多年的小镇岁月,一个女人既要当爹,又要当妈;既要上班,又要顾家,个中艰辛,可想而知。可在我的记忆里,不管多么艰难,母亲从来没有流过眼泪。有一次,不知因为什么事,母亲大声说:“我从来不求任何人,我从来只靠我自己!” 铿锵有力,掷地有声,字字敲在年幼的我心上。
曾听母亲回忆过我出生的场景。那天,母亲夹着一床被子,独自到镇卫生院生下了我。生产完,她浑身血污,没有一件干净衣服可以穿;内急想上厕所,却因产后虚弱,又无人搀扶,只能憋着;饿得前胸贴后背,没人送吃的,也只能忍着。
二十年后,姐姐的女儿出生,父亲呵护备至,不知怎么疼才好。父亲感慨说,现在才有养女儿的感觉,我自己的女儿,都不知道是怎么长大的。
我们知道。那个女人,把她的青春、美貌、温柔和健康,掰碎了、揉烂了,和着一粥一饭,伴着日升日落,一天天把我们拉扯大。那漫长的时光啊。
三
轮船停靠吴淞码头。踏上陆地的那一刹,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。吐了几天、饿了几天的母亲,一进我的家门,瞬间满血复活,精神抖擞地张罗着买菜做饭、拖地扫地。我和她抢扫把,发现她的力气还是那么大。她不由分说推开我,命令我一边歇着。
我知道,母亲有个不曾说出口的原则:有她在的时候,不让她的小女儿做一点点家务。
也许是她一生饱经磨难,也许是她从未得到过父辈的疼宠,所以她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部投射到这个中年得来的女儿身上,哪怕自己落魄潦倒、病痛缠身,也要把她当成公主,捧在手心里疼。
我就是这样长大。虽然家里不算富裕,但从未缺衣少食,更未见识过人情冷暖。母亲尽她最大的努力,呵护我,娇惯我,把我养成一株温室里的娇花。在高中毕业之前,我甚至从未自己绑过辫子,每天早上,母亲都会站在我身后,用她残疾的手,给我梳一个高高的马尾。
那年高考,我远远超过一本线,名字挂在家属大院的喜报上。生平第一次,我看见母亲流泪。她一边开心地笑着,一边用毛巾捂着脸痛哭。她的女儿,用一纸录取通知书,抚慰了她半生的辛酸。
永远记得那个春日,我结束了短暂的探亲,准备回到学校。母亲送我到门口。我虽然已经是大学生,但内心里,还是那个单纯透明、从没长大过的小少女。我站在门外,突然,一股巨大的、莫名的伤感袭击了我。心里有个声音说,我不想离开面前这个女人,不想离开这个生命里最深的依靠。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。
母亲傻了。她手足无措,愣了好一会才走上前,嗔道:“都多大了,还离不开妈?”粗粝的手指抚上我的脸颊。她笑着,笑得很勉强,笑得很难看。
而我终究是走了,走出她的羽翼,走向外面的世界,一去不回头。
四
刚到上海的时候,无亲无故,无根无基,连上海话都听不懂,我所能做的,就是比旁人更加拼命地工作,更加努力地挣钱。那时我在公司有个外号,叫“救火队员”。就是不管什么岗位、什么项目,老板找不到人顶了,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。而我次次都能救得不错,属于不制造问题、专解决问题的一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。
零八年我怀孕。那时我先生也正处在工作的重压之下,为了不给他添麻烦,十月怀胎,所有的产检我都独自去做。早上七点就到医院,自己排队挂号交费,做各种检查,九点钟赶到公司准时上班。绝大部分时候我都应付得来,只有一次抽血,因为手里提满了东西,没有及时按住针眼,血迅速从静脉中喷涌出来,一滴一滴,把地面都洇湿了一块。整个孕期,我没有请过一天假,一直到生产前一周还在工作。产后,产假没有休满,我又急匆匆销假回公司上班。
有一次,我无意中和部门90后的女同事讲起这段经历。我是当趣事来讲的,但突然发现她们个个张大了嘴,眼睛里满是不可置信。那一瞬我惊觉,在岁月的磨砺下,我已经变成了和母亲一样的女人,一样的独立,一样的要强,一样的坚忍。遗传是一件神奇的事情,有些东西,早已通过脐带,深入到血液、骨髓,成为我的宿命。感谢母亲,如果不是她赋予我的这些品质,我不可能在这个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,并深深扎下根来。
五
我到上海已经十多年了。这些年,无论是穷途末路,还是春风得意,母亲从不踏足上海一步。直到我零八年怀孕,母亲才在父亲的百般劝说下,匆匆来沪一晤,小住几天就回去了。这次是第二次。我明白她,她是个骨头硬到极点的老太太,只有在她自己的那个小窝里,她才觉得是当家作主。哪怕在她最心爱的女儿家,她也觉得是寄人篱下,要看女婿脸色,浑身不自在。
而我已在上海结婚生子,此生当不会回归故乡。于是就想出带她去旅游的法子,以表孝心。但现实告诉我,爱她,莫过于让她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,安安静静地呆着,那才是对她最大的成全。
看过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,上面说,人生其实只有900个月,你可以用一张A4纸画一个30*30的表格,你的全部人生都在这一张白纸上。假如你和你的父母一年只见一次面,那么你的余生和他们相处的时间是这样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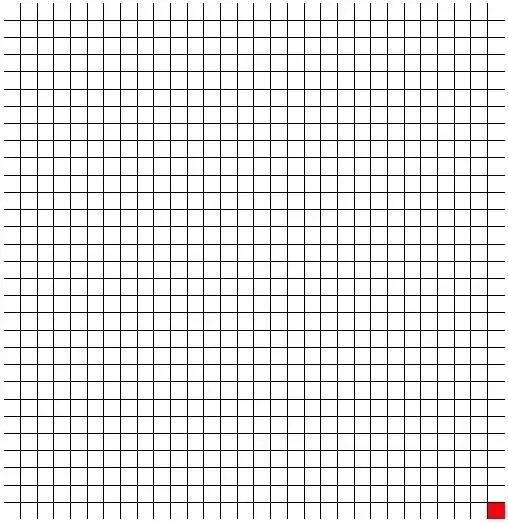
此生,母亲将老死在故乡,而我将一直活在异乡。我们是血脉上紧密相连的母女,却在地缘上几乎永不交集。疼痛难当,却莫可奈何。我想,有如此悲哀的异乡人当不止我一个。
只能遥祝故乡的母亲福寿安康,长命百岁。
更多文章,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“杨柯灯下拾粹”。
0
推荐




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
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